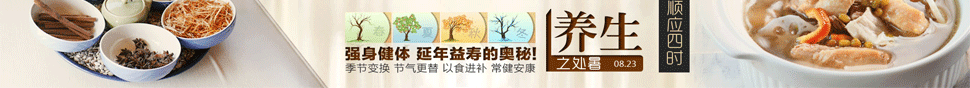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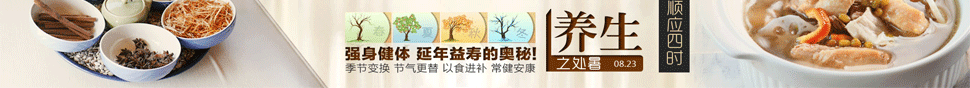
8
宋神宗起用苏轼的心思由来已久,宰相王珪几番阻挠,未能如愿。北宋政坛,王珪是个史家公认的小人,倒不全是因为他在“乌台诗案”中屡向苏轼下毒手。他以见风使舵出名,巴结术炉火纯青。熙宁年间王安石当政,他巴结王安石胡须上的虱子。虱子爬来爬去,神宗也看见了,但没说话。王安石自己察觉了,伸手捉住它,正欲掐死,王珪忙道:荆公且慢,这是一只不同寻常的虱子!安石奇道:何以见得虱子不寻常?王珪说:曾经御览,屡游相须。
王珪培植党羽很有一套,有时皇帝也奈何不了他。元丰五年,神宗想让苏轼修国史;六年,想任命苏轼为江宁太守,都被王珪以种种理由拦下。其时朝廷正向北辽用兵,这事就搁下了。元丰七年,神宗动用不轻易使用的“皇帝手札”,不与执政商量,直接下令复起苏轼。复起的第一步,授苏轼汝州团练副使,本州安置。汝州(今临汝)离汴京很近了。
苏轼依依不舍离开黄州。临皋亭涛声依旧,五十亩东坡麦苗青青,雪堂的离别酒喝了一茬又一茬……“我家江水初发源,宦游直送江人海。”当年在杭州写下的诗句,宿命般画出他的命运轨迹。当官就是马不停蹄,这州三年那州两年的,有时候途中走数月,到任只几十天,又调走了。于是有了“宦游”这类词汇,令人感慨万端。
把宦游列入人类学的研究课题,想必很有趣吧?
苏轼一生,宦游四十余年,足迹半中国。
元丰七年春他起程向汝州,陈慥送他直到九江。这位侠肝义胆的眉山青神县汉子,曾从他居住的歧亭七次到黄州看望苏轼,每次往返四五百里。他和苏轼气味相投,都是古道热肠。还有一个眉山人巢谷,值得浓墨重写的普通人,行事很神秘。苏轼倒霉的时候他总会现身,苏轼得意了,他又飘然而去。
这次苏轼赴汝州,巢谷提前数日不辞而别。却交给苏轼一个祖传药方“圣散子”,叮嘱说,千万不可示人,但关键时刻可以一用。苏轼并未十分在意,他这些年收集的药方多了。
几年后在杭州,这“圣散子”救活了成千上万的疫病患者。苏轼万分感激巢谷,却不知巢谷身在何处。
苏轼现在到了九江地面,陈慥返回,大和尚参廖前来迎接,陪苏轼畅游庐山。山中盘桓多日,诗人哲人合而为一。名山得了名诗《题西林石壁》: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
诗人看山峰却看见人世了。寥寥数语,说尽多少事。
人生就是不断地总结,领悟,参透,千思量万琢磨懂得了一点道理,却已两鬓斑白,再是喜悦也难掩苍凉……
金陵的王安石正苍凉着,变法大业未竟,备受小人折磨,儿子死了,他伤心归故里,隐居于半山,骑驴瞎转,口中不停地念叨着谁也听不清的言语。也许是念叨受苦受难的天下苍生吧,为他的变法失误深自忏悔。
听说苏轼要来,王安石激动了好几天。他亲自到江边迎接,苏轼登岸施礼,说:轼今日野服拜见大丞相!王安石执苏轼的手笑道:礼数是为我辈而设的吗?二人大笑,一句话胜千言,泯去旧日的恩恩怨怨。
王安石苏东坡携手游金陵,促膝交谈不知疲倦。历史,文学,国事,家事,虽然时时有争论,友情却暗生,并且迅速走到阳光下。王安石迫切希望苏轼卜居金陵,朝廷那边由他说去。苏轼感动了,辗转几处买田,皆不如意,只好辞别荆公。
王安石又送别,望着苏轼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:“不知更几百年,方有此等人物!”
历史巨人的话,分量当然不轻。
认识到苏东坡的价值,王安石是第一人。欧阳修对苏轼的评价仅限于文学。而在王安石眼中,苏轼是政治奇人、文化伟人。
苏东坡造访金陵期间却发生了一桩惨事:未满周岁的遁儿夭折于舟中。王朝云悲痛欲绝。东坡写诗哀号:
吾年四十九,羁旅失幼子。幼子真吾儿,眉角生已似……我泪犹可拭,日远当日忘。母哭不可闻,欲与汝俱亡!故衣尚盈架,涨乳已流床。感此欲忘生,一卧终日僵……
年轻的母亲、刚满二十四岁的王朝云,其状之惨,谁也不忍心去详细描述。
也许是丧子之痛,也许是黄州诗意生活的惯性诱惑,使苏轼有了买田隐居的念头。这念头一动,立刻招来八方吁请,范镇请他去许昌,王巩请他去扬州,张方平请他去南都……古人讲究千金卜居,千金择邻,有苏东坡这样的人做邻居,真是一种幸福。东坡分身乏术,为难了。老朋友蒋之奇力邀他去常州,到宜兴的一座山中买田,他去了,买下一块可年供八百石谷子的田地。有了这块地,一家十几口,吃饭是不成问题的。他还有退休金嘛。于是两上《乞常州居住状》,恳请朝廷批准。
过了数月,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,他的欣喜溢于言表。书法兼随笔名作《楚颂帖》是此间写下的:“吾性好种植,能手自接果木,尤好栽橘。阳羡在洞庭上,柑橘栽至易得,当买一小园,种柑橘三百本。屈原作橘颂,吾园若成,当作一亭,名之日楚颂。”
这《楚颂帖》与书于黄州的《寒食帖》,是苏轼书法的两大代表作。后者现藏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,真迹。这可是伟人、文豪、书画巨擘的亲爱书法呀,我想到它,心就怦怦跳。如此绝世珍品,能运送到伟人的故乡展出一回么?
东坡另赋《菩萨蛮》云:买田阳羡吾将老,从来只为溪山好。来往一虚舟,聊从造物游……
阳羡即宜兴,东坡待在这地方,溪山美朋友多,杭州、扬州、金陵等地,朋友往来很方便。活动半径大,日常韵味足,具有相当完整的“生活世界”。它对东坡的吸引是不言而喻的。另有一层,却为朝云考虑:家庭生活安定了,不复舟车劳顿忽东忽西,她或能再生一个孩子,重新做母亲。
东坡为自己、也为家人勾勒了未来生活的图景。
然而朝廷又生大变故,刮起了新政旋风。苏东坡在常州忙着规划诗篇栖居,这旋风移动速度奇快,刮到他头上了,刮得他离地三尺随气流飘荡,手中的规划图不知飞向何处去……
宋神宗驾崩,小皇帝哲宗只有十岁。高太后摄政,改年号为元祐,显示出对仁宋嘉祐时代的强烈向往。
高太后发起“元祐更化”,找谁来辅佐她呢?
洛阳的“独乐园”,一位老者埋头写巨著,转眼便是十五年。他就是司马光,王安石的老对头。关于独乐园,宋人笔记多有描述,它既是史学中心,又是隐形的政治枢纽,各类政要络绎不绝。司马光字君实,人称温公。他是公正而温和的大人物,像王安石一样不近女色,平时有点不苟言笑,但并不呆板。有个幽默故事:他夫人上元节想到街上看灯,临走时跟他打个招呼。他说,家里不是有灯吗?夫人笑道:街上人多热闹,名为看灯,实为看人嘛。司马光眼皮子一翻:莫非老夫是鬼呀?夫人顿时乐了,出门后跟其他贵妇嘀咕,这故事很快传遍了洛阳。
在一般百姓眼中,司马君实几同圣人。他到京城,若是被人发现了,一定会发生交通堵塞。王安石熙宁变法,由于来势太猛而祸及城乡,所以民众对马司光寄予厚望。
司马光组内阁,上表推荐人才,苏轼赫然在册。另一个大臣吕公著,也向高太后推荐苏轼。高太后真是喜上眉梢。喜从何来?她一向对苏轼青眼有加,只碍于神宗,不便插手朝政。神宗一去,她垂帘听政,正考虑用什么方式起用苏轼,却接到两个重臣不约而同的推荐,她不高兴谁高兴呢?如果她夹带了一点私心,不便立刻重用苏轼,那么司马光、吕公著的荐表,确实来得正是时候。
高太后下旨,任命苏轼知登州(山东蓬莱)军事州,掌军政大权。苏轼领旨谢恩,但在给朋友的书信中,表明他反应平淡:“一夫进退何足道。”他又得调整心态,撇下刚买的宜兴田,隐藏了苏东坡,而让“屡犯世患”的苏轼再度粉墨登场。
前路说不准。却总得上路吧。
走了三个月,登州任上仅五天,新的任命复至:升苏轼为礼部郎中。全家人床还没睡热呢,又起程了。
不过苏轼动作快,五天干了两件大事:请求朝廷变更当地的军事部署,免除食盐专卖。后者源于他的一贯主张:民间贸易自由。盐、铁、酒、茶的专卖他都反对,而且走到哪儿反到哪儿,手中无权就挥动诗笔。他终极的政治理想是富民强国。
伟人的调头何其干净利落!归隐田园,以后再说吧。
他还抽空到海边看了海市蜃楼,写下长诗《海市》。
刚到京师,他升为中书舍人,在宰相手下干活。半年后,再升翰林学士知制诰,负责起草圣旨的工作,官三品,位在六部尚书之上。升迁如此之快,百官为之瞩目,苏轼自己也晕头转向。他刚五十出头,居翰林院要职,这不是明摆着要当宰相吗?中唐及北宋翰林院,均被视为储备宰辅之地。而苏轼具备宰相的才能,宋仁宗早就讲过,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司马光年迈,身体又不好,君实一旦退下,子瞻定会补缺……朝廷这些议论,其实对苏轼不利。返京不到一年,他成为舆论的焦点,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://www.goujif.com/gjgx/11493.html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