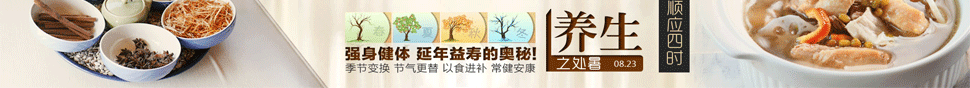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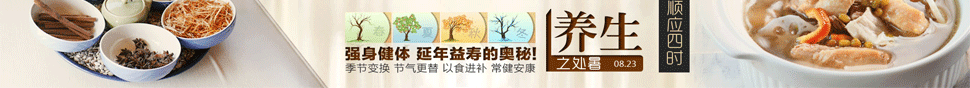
这一年()
晚上躺在床上,右手扣住左手的手腕,拇指触到了中指,心一惊:瘦了一圈。二O一九年的关键词,确实是"病”这个字了。
突然发冷,接着发烧。这种情况不常发生,但是这两年来却偶有发生,不清楚怎么回事,往往是抵过去就好了。心里想着不妙,却也不知道怎么办,双十二那天,白天上班依旧如常,晚上赴一个宴,没敢喝酒,回到家,没什么异常刚,只觉有些疲惫,有些冷。睡觉的时候,开始冷得发抖(俗谓"打摆子”),然后就是发烧。
这一次,却没像往常那样抵过去,半夜,左膝盖开始疼,一直到天亮。上班时,左脚瘸了。
今年,看着到了十二月,心想:医院躺病号了。谁曾想,还是逃不过。住院十来天,反反复复。医生说,怎么办呢?这里能用的药已经用了,实在不行,你还是去贵阳打生物制剂吧。这话让我想起了去年的经历,医院住半个月,医生说,实在不行,医院看看吧。医院医院(陆军医院),可是,现在,医院路程远,而是我才三十一岁,还不想走到用生物制剂的地步。一个月三四千的生物制剂费用,活着还有什么意义?
命途多舛,突然想起这个词,其实,想想从涉世以来,我的人生,除了多病,途路也算安平。只是三十岁以来,毫无而立之感,尽是骨疏松之觉。
苏子说: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
有时想想,从宏观处看,人生天地间,确如蜉蝣一粟,何其渺小。很多时候,我也这样看人生。病多后,却慢慢变得喜欢从微观处想,一切病,都是身体的微观出了问题。对于宏观,很多人都能谈天说地,而对于微观,人总显得无奈。
这一年,遇到一些人,做过一些事,感谢不屑与关心,感谢羁绊与帮助。以后最希望的,还是都匀这地的医疗水平能够提高一点吧,不要动不动医院看看。
今夜,医院跨年了。
逃离乡镇
到九三学社都匀市委上班已经一个多月了,回顾来路,有些话想说一说。
题目用了“逃离”的字眼,对我来说,有几分写实。算一下,只数年,我在乡镇呆了九年,数到月,那就要在九前加一个近字。无论是九年还是近九年,这个数字,与在乡镇干到退休的比起来,实不足道,与走马镀金的比起来,也可以说是一段有点长的岁月。
二〇一一年夏,我大学毕业。在此之前,我原本想着考研,而且报了名,但想想家里的经济情况,最终没去考试。于是,在毕业那年的四月二十四日,我参加了贵州省公务员考试。报名的时候,因着对社会现实的不了解和对找到工作有碗饭吃的渴望,考虑的只是离家近一点,我便报考了坝固镇的职位。
我也曾有过考上家门口单位公务员的兴奋,然而,更多的是入门之后的无奈与不甘。无奈来自面对应接不暇、繁忙杂乱的工作,身心疲惫,不甘来自本可以离开却因领导的羁绊而残留的一点希望。这无奈和不甘,成了我想要逃离乡镇的思想动力。
为什么逃离乡镇?
我想逃离能力不足的尴尬。二〇一七年一月,幸得领导垂青,在经开区坐了两年多机关办公室之后,我到洛邦任职。在洛邦,我开始包村,即所谓的包村领导。我先后包附城村、绕河村,包村的工作,多是脱贫攻坚的事情,还少不了村里群众的纠纷矛盾。那时的洛邦,在开发区的开发中,产生了很多矛盾,这些矛盾相互牵连、极其复杂,从而有一部分群众常常采取上访等形式寻求解决。正是在洛邦,我有机会第一次到了北京,虽然是为了截访。所有的矛盾纠纷,都需要耍嘴皮子,与群众唇枪舌剑、谈说道理,需要很好的口才,而我天生是个嘴笨的人,在这些工作中,很感吃力。在包村工作中,需要统筹协调好村干部,而我的性格稍弱,组织能力也显欠缺。所以,我想逃离,免得总是让能不足的尴尬伴随日常的工作。
我还想逃离繁杂琐事的羁绊。我是个性格散漫的人,不热衷迎来送往,不擅长站位攀附,有一点点社交恐惧。所以,有人赞我能力如何时,我会感到惶恐,有人觉得我不行时,我反而会暗暗窃喜。这些,均源于散漫的性格与繁杂琐事的格格不入。有人请客,我会反复想着找个合适的理由推脱;到了节假日,总期盼着天气阴雨连绵;夜晚的暴雨,会让我在家坐立不安、不能睡眠;各种诸如非洲猪瘟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应急事件,也需要置身参与,践行着“五加二、白加黑”。事实上,我对理想人生的追求,不过家与诗和远方,所以,我想逃离乡镇的嘈杂。
二〇一八年,我因脖、背、腰、髋关节、四肢等疼痛,先医院、医院、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医院,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。这个病并不能要人命,只是发病时会影响正常生活,严重会发展为畸形残疾,目前没有可以根治的方法,只能靠长期使用药物维持。由此,我更想离开乡镇,因为按照当下乡镇的工作量,畸形残疾并不是没有可能。二〇一九年年底,随着市里要求周末开展“帮扶日”,工作处于天天上班的状态,我心里想着:医院。果然,十二月十二日,白天正常上班,没什么异常,只感有点疲惫;晚上,赴一个宴,回家后只感觉有点冷,睡觉时冷的感觉加重,全身发抖,接着就是高烧。第二天,左腿便伴着剧烈疼痛,瘸了。然后,便是辗转住院,在医院度过跨年夜。
这一切,让我在心理多少产生一点害怕,想着还未清的债务,还未得养天年的父母,还有妻儿,我觉得真是要想办法逃离乡镇了。
二〇一七年,机缘巧合,我认识了九三学社都匀市委宋萍副主委和吴亚静吴姐,然后加入九三学社。后来,经开区体制改革,人事变动,那段时间很多人都在找地方调,我便向宋萍副主委表示想去社市委工作。由于编制有限,那时没有调成。直到二〇一九年年底,吴姐退休,编制空出,宋萍副主委再次问我是否还有意到社市委工作,我欣然答应。在此之前,二〇一九年年初,市纪委曾与我联系,问我到纪委工作的意愿,为了离开乡镇,当时我甚至答应到纪委工作后即入党(我当时觉得到社市委工作的可能性很小),单位的领导却认为我的身体状况不能承受纪委的工作,代我搪塞过去,没能去成。现在,我挺感谢这没能去成。
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,我正式到九三学社都匀市委上班,卸下了在乡镇时背着的没有芝麻绿豆大却责任不轻的所谓实职,实现了改非——九三学社都匀市委员会三级主任科员。我曾向组织部申请说,如果因为这个小小的副科级不能调动,我愿意以普通科员的身份调动。组织最后还是为我保留了体面。
这些年一路走来,遇到很多人,遭遇很多事。这些人与事,有关心、有不屑,有提携、有羁绊,有鼓励、有嘲讽,对我来说,都是在助我不断进步,我都要一一感谢。
以后的时日,还很长,我只是希望尽自己的力所能及,把本职做好,不至于成为真正的废柴,再让生活多一点味道。
苏东坡说: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世事纷繁,我的理想,也只不过如此。
“空手空脚”帮扶二三事
年2月5日,农历腊月二十,正在匀东镇绕河村参与处置民房失火事件的我,接到一个曾经帮扶过的贫困户的电话。接了电话,他没有寒暄,没有客套,向我耳边直接甩来一句质问:
“马上过年了,你哪天送东西来我家?”
这个问题,让我哭笑不得。那个时候,我的帮扶任务已经调整到绕河村,不再帮扶他。我只得告诉他,让他去村里咨询一下,看是否有政策性的物资物品。
然而,仅过了整整3个月,年5月5日清晨,我被一阵手机铃声从梦中惊醒。拿起手机一看,又是他。接了电话,依旧没有寒暄,依旧没有客套,他说:
“我没钱了,给我点钱用。”
听得出,他的口气很坚定,像是在要债。那一刻,我的血液直往头顶冲。压制住怒火,我问他:“你要多少钱?”
“块。”
这个数字,让我的怒火忍无可忍,我问了他一连串问题:
“你是我家哪个?我为什么要给你钱?你好手好脚,为什么不出去找点活干?”
电话那边一阵沉默,然后挂断了。
那以后,我没有再接到这样的电话。经过反思,我认为,出现这样的状况,与我自身有很大关系。帮扶之初,帮扶任务并不多,也就两三户。因此,每次下村,我都会买一些东西,或水果,或大米,或食用油,提着入户。当然,大部分群众对此是感激的,但是,也有人觉得这是他该得的,理所应当的,渐渐的,就有了惯性。
后来,我的帮扶任务从3户变成4户,由4户变成5户,最后在年9月增加到9户,即绕河村5户、马场村4户。这个时候,继续提东西入户,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,而且,接了那两次电话之后,我也开始怀疑提东西入户对帮扶的有效性。于是,我决定采取“空手空脚”的方式走访帮扶。
初次入户,我什么也没带就去了。每到一户,我都要提之前那两个电话的事,并告诉帮扶户:“只要有政策,只要符合条件,我一定为你们去争取、办理。”听了我的诉说,9户帮扶户都表示理解。
“空手空脚”的帮扶,也让我遇到了麻烦。年9月,我接到马场村的帮扶任务后首次走访,到老唐家的时候,他对我的到来表现很冷漠,问他家这几年有没有享受什么政策,他都说什么也没得到,言语之间充满抱怨和不满。经过耐心交流,我发现他的不满所在。原来,他的女儿在读高二,却没有享受到教育资助。他的这个说法当时让我有些疑惑,因为根据他家的一户一档资料显示,登记的家庭人口为3人,即夫妻二人与其儿子,并没有女儿。
这个情况,让我意识到这户可能存在漏人的问题。经过核查户口信息,确定老唐确实还有一个女儿在匀东中学读书,但是由于一直没有在贫困系统内,这些年都没有享受到教育资助。这件事让我很吃惊,也让我对村里的工作有些不满,我找到村支书了解情况,村支书支支吾吾说不清楚。我只得立即填写人口增加表,将老唐女儿的信息上报匀东镇扶贫办。没过多久,老唐的女儿进入了扶贫系统,并顺利办理了教育资助。当我再到老唐家的时候,老唐夫妻已经是笑脸相迎了。
“空手空脚”帮扶,让我觉得更要注意让帮扶户真正享受政策,同时要想方设法激发帮扶户自身的内生动力,实现真正脱贫。
绕河村的老杨家,是低保户,老杨夫妻已经70多岁了,有一个30多岁的儿子,赋闲在家,不干农活,也不出去找活干。
刚开始的几次走访,都只遇见老杨夫妻,没见过他们的儿子。每次走访,老杨夫妻都说儿子有病,而且是精神方面的问题。我当时也信以为真,并在记录他家的家庭情况时,将他儿子表述为有精神障碍问题,不能劳动。有一次,我与村干部一起走访,因为觉得老杨家确实困难,那天我便买了一桶油,结果没有遇到老杨夫妻,倒是遇见了他们的儿子。一番交流下来,这个比我年长几岁的年轻人完全不像是老杨夫妻说的有精神问题,只不过是个身强力壮、不想干活、怕见生人的年轻人而已。在回来的路上,陪我一起走访的村干部说:“他本来就没什么问题,只是懒而已。”
原本以为老杨家三口人没有劳力,只能靠低保过着紧凑的生活,这次走访让我觉得老杨家还大有希望。此后,我便打起了老杨儿子的主意——动员他出去找活干。在后来的走访中,我与绕河村多名村干部先后去走访老杨,做他夫妻的思想工作,让他们首先转变思想观念。
我对老杨说:“你们现在已经这么大年纪了,本来就应该由儿子来承担家里的农活,照顾你们,结果你们还一直像对小孩子一样对儿子,这对你们没好处,对儿子更不是好事。他现在还这么年轻,应该出去找些活路干,不能老是呆在家里。出去找活干,不仅可以看外面的世界,也可以赚点钱,有了钱,再娶个媳妇,家里的情况就会慢慢好起来。如果你们还照现在这样下去,以后你们老了、干不动活路了怎么办?你们的儿子又怎么办?”
经过一段时间的轮番入户做工作,老杨夫妻被说动了,他们儿子的思想也有了一些转变。终于,在年下半年,老杨的儿子去了广东打工。回来过年的时候,我再遇见老杨的儿子,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可以用焕然一新这个词来形容:穿着不再邋遢,边幅不再凌乱,精神不再萎靡,也不再怕与生人交流。
这样的改变,让我对自己的帮扶充满信心。
除此之外,我还“阻挠”了老杨家在年脱贫。老杨家住的木房属于危房,当时已被列为危房改造对象,但是却迟迟没有落实。年,村里在报拟脱贫名单时,将老杨家列入其中。我知道后,即以帮扶责任人的名义,分别向绕河村村委会和匀东镇扶贫办上报书面说明,表示在老杨家落实危房改造之前,不能脱贫。同时,我还找到当时的匀东镇党委副书记,反映了老杨家的情况。最终,老杨家没有在年脱贫,直到年,他家的危房改造终于完成,才顺利脱贫。
从年底参与帮扶以来,我先后帮扶过20余户贫困户。在这过程中,我没有为帮扶户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,只是以将心比心的态度,用心交流的情感,吃准政策、利用政策,在“空手空脚”的帮扶中,为帮扶户做好力所能及又微不足道的小事情。尽管如此,我依旧为能够亲身参与脱贫攻坚这一时代大业而感到自豪,在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中,获得了不一样的小确幸。
写给过去的一年()
一
过去的一年,过得很匆忙,也很漫长。
说匆忙,是因为这一年好像只是年初发生了一场新冠疫情,疫情还没结束,转眼一年就过去了。说漫长,这一年好像除了没有结束的疫情,世界还发生了许多事。
正如人们形容的那样,年注定是“极不平凡”“不同凡响”的一年,难怪牛津词典竟选不出这一年的年度词汇。
就个人来说,也很难用一个字或一个词归纳过去的一年。
这一年,工作笔记写了两本,其中的内容,大半与新冠疫情防控有关,此外就是脱贫攻坚,其中也记录着很多杂事、乱事和无可奈何的事。
年底到年初,我因强直性脊柱炎病发住院,期间看到新闻,说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,当时报道说没有人传人的证据。谁承想,在除夕前几天,态势转恶。于是,拉开了人心惶惶的疫情防空大幕。
还记得,那段时间除了参加镇里安排的值班,便天天蹲守在幸福村,安排驻村干部、村两委干部每天排查人员、上报信息、消杀市场……。与村支书开着车,放着广播,走村串寨,重复播放防控广播。那时要求晚上不到十点不能回家,我也就每天十点之后才敢离开村里。事实上,回了家也不敢睡,因为随时都会有指令,得到指令就必须核实信息,核实好了还要立即反馈上报。所以,那些夜晚,都是过了十二点才敢睡下,有几次甚至在凌晨返回村里。
还记得,那个时候学校没有开学,我们便把子夏送至小桥边父母那里。伊抽调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,我在乡镇,有时她睡了我没回家,有时我回家了她还在指挥部,两个人在那段时间也难面对面说上几句话,联系几乎都是上班期间通过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://www.goujif.com/gjjg/11155.html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