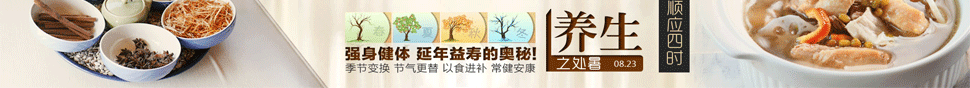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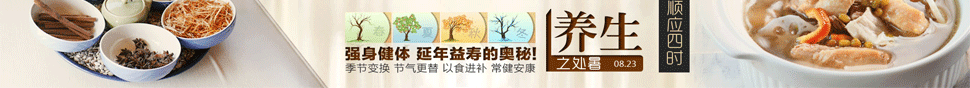
散文
乡愁三则
/陈弘志
故乡官井村边头
捣黑楞村是个挺团全的村落,有前街后街东头西头之分。全村有三口官井,一口官井在前街东梢,供前街和东头饮用;一口官井在尽西头,供西头村民饮用;一口官井在后街,供后街村民饮用。所谓官井就是全村所有,不是哪家的私有财产。凿井一起凿,淘井一起淘,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。平日的维护,也仰仗众人。
后街上的这口官井,离我家院子不远,大概有百步之遥,官井东头有一苗老榆树,长在草坯围起的高圪塔上,枝分五杈,绿荫如盖。紧靠井台的高墙里,是蒙古人常家的树园,墙角有个水道,作灌园之用。到了清明时节,园里杏花开了,粉白粉白的花朵,一枝枝探出高墙,装点着繁忙的井台。
高圪塔上的老榆树,榆钱儿结得繁而大。嚼在嘴里,甜丝丝的,有一股清香,令小孩垂涎。大一点的孩子有办法,把镰刀头装在长杆上,做成了挠钩,往下钩扯榆钱儿。当然得趁晌午没人时,方能偷偷摸摸进行。如果不这样做,只能碰运气了,等树上的黑老鸹起落时,总会有蹬落的榆钱儿枝。仰着头瞅着呱呱的黑老鸹,时间长了脖子挺不得劲。
井台是石头铺砌的,红的红青的青,磨得非常光滑;水斗子是柳编的,一斗子水盛半水桶,下湿地水位挺浅的。井台前斜放着一个大石槽,是早晚收工后饮牲口的。石槽左近一片黑乎乎的污泥,不时有家燕儿胡燕儿过来衔泥,它们呢呢喃喃吵闹着,一嘴一嘴地运送着筑窝。
家燕儿有时将窝筑在屋里,筑得小巧玲珑非常精细。村上的孩子,从小被教调,不能欺负燕子,不能捅咕燕窝。每逢清明时节,还蒸一些寒燕,插在圪针枝上,迎接归来的燕子。
村上缺医少药,一旦碰上病痛,只能胡乱对付,有时碰巧好了。一年初夏,窗扇已开。我站在家里的窗台上,观看燕窝里的小燕,仿佛可身只长着个大黄嘴岔,等待着大燕子含回食物来喂。猛地看见一个蜂巢,窟窿眼儿满是蜂蜜。一时嘴馋,酿成大祸,图蜂蜜没吃上,脑袋蜇得膀肿。这该怎么办呢?用官井污泥糊。虽然味道不好,却挺管用的,消肿解痛,很快好了。
庙宇戏台古榆树
旧时并非每个村落都有庙宇,庙宇是信仰和文化的标志。在方圆十几里的城东,唯独捣黑楞村有庙。这是一座龙王庙,坐落在村东北角。庙院不算大,但应有尽有。正殿三间比较高大,重檐立柱,筒瓦吻头。阶除高台,神圣庄严。庙里泥塑龙王爷龙王奶奶,前面置以长条供桌。摆放香炉烛台,以及祭祀供品。
神像背后和两侧的墙壁上,用墨色绘制着三幅壁画,两面好像是四季农耕,画的是春播夏锄秋收冬藏,正面是风起云涌神龙摆尾,画的是各路神仙行云布雨。雷公手里拿着斧錾,每敲击便雷声滚滚;电母手里拿着面镜子,每晃动便电光闪闪,风伯鼓吹,满天云烟,雨师行雨,普降甘霖。
庙院西南角是鼓楼,置鼓一面,东南角是钟楼,吊钟一口。晨钟暮鼓,各司其职。正中为山门,平素不开的,门闩插得死死的,人由旁门出入。紧靠着正殿,有老道住房,还有东厢房两间,存放庙里杂物。庙院里有四五棵老榆树,长得枝叶婆娑荫翳蔽日。老道住房是里外间,外间是旧时村社议事之处,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也办过学堂,挂过农会乡公所的牌子。
庙前是一个土广场,与山门遥遥相对,是一座高大的戏台,儿时觉得戏台很高,看戏要仰着脖子才行,台口砖雕出将入相字样。戏台分前台和后台,前台是演戏的地方,后台是化妆的地方,观众不得进入后台。戏台和山门之间,长一苗古老榆树。树干几个人搂不住,桠桠杈杈虬枝盘旋。庙宇古树戏台,成为村里景致。
村子里的人们,除了上香祭祀,一般不登庙门,但凡上庙里去,肯定有难解事体,要去排解纠纷。旧时的郊野荒村,真是山高皇帝远。家族内部起了纷争,娘舅老者出面调停,本着家丑不外扬的理念,家族内部了断息事宁人。人们不去见官,不懂得打官司。
村民邻里有了矛盾,要按乡规民约理论。就得上庙分辨是非曲直,由村里德高望重者评判。虽然不是法庭,但是颇具权威。侵犯了邻居权益的,就得向邻居赔不是;侵犯了公众利益的,就得向全村赔不是。除了物质处罚之外,还得给庙上添置宫灯,每逢年节唱戏,挂在戏台檐口。
戏台上发生的事情,对于孩子们而言,虽说有些印象,但都浮光掠影。戏台是我们玩耍的地方,那里的砖缝里有蚰蜒,不用一个时辰,就能扣好几条。民谚云,蚰蜒狗脊钻进屁股扭捏,但凡穿开裆裤的孩子,老人总提醒不能赤地坐,就是为了这个的缘故。而这两种虫子是逮鸟的好诱饵,将其拴在马尾编成的鸟套子上,可套住青红雀、麻壳子和虎伯劳,有的鸟可以养熟,有的寻死觅活的,养上几天就放了。
广场上那棵老榆树,结的榆钱有铜钱大。一枝挨着一枝,一簇挨着一簇,鹅黄颜色,水嫩欲滴,一阵和风吹过,散发甜甜香气。这苗老榆树长得很高,树干几个人搂不住。小孩子想上去,连门儿也没有。好在树上有好多黑老鸹,正是它们修巢孵蛋的季节,衔着柴草,飞来飞去。黑老鸹在树上起落,总会有踩断的树枝,掉落下来砰然落地,便是一枝又繁又嫩的榆钱,大家一人一截分着吃,然后再仰起脖子傻等。
有一段时间,庙里是学堂。每逢人们出工,牛羊进滩时分,村里异常安谧静悄,偶然听到鸡鸣狗叫。这时庙里传出琅琅书声,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朗读,而是有腔有调的吟诵,与其说是念,倒不如说唱,声音抑扬顿挫,听来很是悦耳。现在想起,颇具古风。
教书先生叫郭怀仁,一开口满嘴是文词儿。那时节时兴喇叭筒读报,郭怀仁开头语便是:农人众乡亲,大家忙忙碌碌云云。村里人的口头语是忙乱,或者称为忙头拾乱,头一次听忙忙碌碌,大伙儿又失笑又不解,于是给他起名“忙忙碌”。
村里的庙宇戏台老榆树,大概是“文革”中彻底消失的。我记得庙里有几块碑碣,记录着龙王庙修筑的缘起,碑阴上刻着字号和人名,还有人们捐钱的多寡。那时小不识几个字,只是觉得字刻得好看。我上小学就出来了,问那些碑碣的下落,说是早不知去向,也许做了房屋根基。一位乡村医生告诉我,石碑是嘉靖年间立的。
家乡草滩莽苍苍
捣黑楞的村前村后,有两条川流不息的河。南面隔河相望,是六犋牛村;北面以河为界,是布塔气村,中间的距离,都是二三里路程。捣黑楞村东是东巴栅,距离有二里地;西南是古路村,距离也是二里地;正西是西巴栅,路程有点远,六七里之遥,村前有小河,柳树颇繁茂;西巴栅村东北,相距二三里,是辛家小营子,地势比较低洼,再往西便是小厂圐圙。如果以捣黑楞为中心观之,这片呼和浩特城东的郊野,除了白塔以东的四村水地而外,这块地界算是人烟稠密的所在。
村南的河床比较宽阔,在枯水季节里,行人可以趟水往来,往来交通并无大碍。到了大暑小暑时节,河水能涨到齐腰深。五十年代中期一段时间,捣黑楞归喇嘛营乡管辖。那时我家老二老三在城里念书,为了减免学杂费申请助学金之事,我母亲步行往乡里探问可否。走到村南河边正要拄棍涉水,河对面的本家梆榔叔看见,急忙叫停道:“大嫂不敢!我来背你!”梆榔叔是我三曾祖的后裔,他们一直住在六犋牛村。那天的河水,没过人腰窝,而且流速湍急,人下去站不稳。于是我母亲顺利过了河,从乡里回来时,梆榔叔搭照着,又把她送过河才回家。
村南除了花花搭搭的田亩外,是一片略带盐碱的平坦草滩。草长得稀稀疏疏,一般来放羊的较多。在抗战胜利之后,我父亲联合邻村乡绅,成立了水利董事会,用“以工代赈”方式,在河畔开凿了永济渠。酬劳以美国面粉结算,是由救济总署提供的。这条永济渠工程挺成功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旧使用着。家里曾经有十几张照片,记录了踏勘挖渠放水的情形,在年红八月前夕,被我架在灶膛里全烧掉了。
南滩里有宗特产,是外地所没有的。那就是著名的河炭,河炭又称泥炭或草炭。它的煤化程度是最低的,是原始状态最初级的煤。河炭形成的自然环境,是常年积水的低洼地带,河炭成因的物质基础,是来自植物残骸的累积。一种是就地生长的薹草属、芦苇属植物,一种是河水冲积而来的残枝落叶。经过多年堆叠积累,就形成了这种河炭。后来知道,河炭是绿色的有机肥料,也可以作为化工业的原料。可当年人们挖取河炭,却是一门心思晒干烧火。
常言道,烧在前,吃在后。柴米油盐,柴字当先。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,家乡人烧火做饭的燃料,主要是柴草和干牛粪,到了冬天,富裕人家,买无烟煤面,和黄土成膏,架起细细火筒,既烧炕也暖家。一般的人家,家暖一盘炕,冷得厉害,炽炽干锅。那时的柴草,要在秋天打好。苍耳子、沙蒿、落林,晒干了都是好烧柴。另外庄稼秸秆,诸如茭子秆、麻秆,都是上好柴火。倘若还不够,就得打茬子,搂毛毛柴,那是冬春之事。
到了深秋时节,地下水位降低。收秋了毕,农事不忙,正是挖河炭的时候。这是一件风火之事,挖开表土,露出河炭,就得赶快往外拾掇,如果稍有腿迟脚慢,地下水就漫上来了,虽说在水里也能打捞,但是凉风习习,坚持不了多久。所以挖河炭需要好人手,那得精壮后生相伴才行。开方之后,铁锹如刀,一锹河炭扔出,便是小半箩头。待到有水浸出,已经大功告成。河炭除了黑,并不像煤炭,条条缕缕的,有许多枝蔓。待到河炭晒干之后,成为一堆黑黢黢的柴火。
村北的草滩,另一番景象。以北滩为坐标,东面是东滩、小东滩;西面是西滩、大西滩。南北三四里,东西十几里,在这么一个范围之内,一个草滩连着另一个草滩,而且一个个泉眼,一道道河槽散布其间。遥想当年捣黑楞,草地就在村畔畔上,还用得着翻过大青山,去四子王旗看草地吗?
江南三月,莺飞草长,一夜春风起,绿尽天涯路。在我们塞北,春天来得晚,但是,来得大气,来得红火,挟着风尘,挟着冷雨,在人们不觉意工夫,悄悄展现出绰约风姿。于是,在无边无际的草滩上,染出一片鹅黄,涂出一片嫩绿,那连片的菅草,转眼变成深绿。
也不知什么缘故,草滩上黄花居多,除了蓝色的马兰花之外,沼泽地遍野的金盏盏,河漕边匍匐的河萹蓄,高坡上挺立的蒲公英,开的都是黄花。那金色的花朵,把太阳的光泽,倾泻在草地上,非常灿烂,非常耀眼。这片肥美的草甸草原,非常适宜于放牧牛马。
七九河开,八九雁来。大雁、胡燕、野鸭、天鹅、红雀、蓝靛、黄雀、伯劳等各种候鸟,或早或晚按时按点地从南方回来,有的打尖住店,在河滩盘桓几日,有的繁衍后代,要一直待到落霜。它们或者出没在草滩的马莲丛中,或者嬉戏在河槽的芦荻深处。婉转歌鸣,令人神往。叫天子在半空哨哒,猛然间垂直降落,你记住它的落点寻去,在草丛下总有一个鸟窝,用马尾毛和柴草筑成,轻柔干燥非常精致。
有一年初春,天气还很冷。二宽叔逮回一只大雁,好像是翅膀受了伤。大雁在天上飞,看起来并不大,放在家地下,就显得硕大。民间传说云,大雁失偶后,就再不相配,为雁群守夜。民间打牲的,一般不打大雁。这只离群的大雁,将息几日养好伤,二宽叔送它到北滩,解开绳索放生了。
草滩的河槽,遍是泉眼,泉水汩汩,四季不竭。河槽不深,没过小腿,河槽不宽,一跃而过。这些涓涓细流,从我们村发源,向西南流淌着,先归腻丹河,后入小黑河。河槽里有明虾、鲫鱼、河蚌,还有两根胡须的鲶鱼。村里人不懂得吃鱼,捞回去水缸里养着。除此而外,还有红腿的锦鸡蛤蟆,这是一种少见的田鸡。
当然还有蟾蜍,和泥土一色,呆头呆脑,满身疙瘩。有一次,我看到一只蟾蜍,足有尺盘大小,眼睛半天一眨,惬惬吓了我一跳。村里有“癞蛤蟆躲端午”的说法,我曾经在端午节清晨去滩里验证。说来也挺奇怪,平时蛙声四起,这会儿十分寂静,竟不见一只蟾蜍的踪影,也许是清早天凉,蟾蜍还没有出工吧?
北滩一到冬天,便是无际的冰凌。一场大风过后,沙土遮盖冰面。等到大风停歇之后,夜间溢出的泉水,又铺开一片新的冰凌,晶莹剔透明镜一般。这里是村里娃娃们的乐园,溜冰打忽触儿的好去处。村里到了腊八节,家家粪堆要立冰山。村里的年轻人便相邀结伴,来这儿红红火火地去砸冰。砸得冰块儿越大越好。大伙把砸好的硕大冰块,运回各自的大门外,矗立在各家的粪堆之上。
本文刊于年《草原》第2期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://www.goujif.com/gjgx/8132.html


